《大風殺》為何叫好不叫座
摘要:白客通過“對不存在的人傾訴”,將夏然用想象填補恐懼的心理層層剝開。“她幫夏然既是出于善良,也是對現有生存秩序的反抗。”從忙崖小鎮的封閉空間到角色的心理牢籠,《大風殺》在暴力的外表下包裹著對現代人精神困境的關懷。
三名警察,一把老式手槍,對峙幾十名持槍悍匪:這場力量懸殊的對決,結果真如看起來那樣毫無懸念嗎?日前,張琪導演的新片《大風殺》在北京國際電影節中戰果頗豐,入圍天壇獎主競賽單元后,將最佳編劇、最佳男配角兩項榮譽收入囊中。
雖然有獎項加持,更有監制江志強此前盛贊成片品質“完全超出想象”,然而《大風殺》票房表現卻并不理想。截至5月7日,這部五一檔期國產新片中評分最高的作品僅收獲了3480萬元票房,在同期九部電影中僅排名第七。這部具有作者性的國產類型片在市場上的處境似乎像它故事中的設定一樣,也被“困住了”。
當“孤島”成為人性的試驗場
《大風殺》將故事背景置于1995年,全面禁槍前一年的西北棄鎮忙崖。“一把槍對幾十條槍”的絕境使影片兼具西部片的氣質與香港警匪片的節奏。導演張琪透露,自己對“極端困境下的人性爆發”有濃厚的興趣,這也是他創作《大風殺》的初衷。“荒漠當中方向太多,反而讓人被困住——我想探討的是,我們到底被什么困住了。”這座被黃沙包裹的“孤島”,既是物理意義上的封閉空間,更暗喻為劇中人的精神困境,似乎人人都在生存本能與道德良知的夾縫中艱難喘息。
影片通過“鋼絲捆綁”“車門斷腕”等生猛場面沖擊感官,卻以聲音、剪輯和畫面的留白激發觀眾想象。夏然與悍匪對峙的槍戰夜戲中,黑暗中閃爍的火光與子彈呼嘯聲比直觀的血肉橫飛更具心理壓迫感。這種“暴力美學”的背后,是創作者對生死的坦然。在張琪看來,“死亡在生活與電影中都是必須直視的命題”。
人心中的“困獸之斗”
白客飾演的民警夏然是荒漠中的孤獨守護者,也是被創傷記憶囚禁的“困獸”。“拍攝時多杰這個角色被設定為‘不存在的人’,他其實是夏然死去的一個戰友,是夏然想象出來與過去對話的媒介。”夏然對戰友的依賴,實則是拒絕直面創傷的自我欺騙。白客通過“對不存在的人傾訴”,將夏然用想象填補恐懼的心理層層剝開。直到最后,戰友提醒他放下時,夏然才慢慢完成從“困在過去”到“嘗試自愈”的蛻變。
李紅是全片最具悲劇色彩的角色。她看似擁有“選擇的權利”,卻在現實中淪為命運的囚徒。對于她的結局,飾演者郎月婷剖析道:“‘我走不了’這句臺詞,不是不能逃,而是一種絕望。”當她發現妹妹已經死去,與惡人同歸于盡成了她唯一能主動掌控的“選擇”。這種在絕境中迸發的自主性,讓角色超越傳統犯罪片的“惡女”框架。
在郎月婷看來,李紅的復雜性在于她游走于黑白邊緣的矛盾身份。她經營著美食城,本有正常生活,卻因北山的歸來重新陷入深淵。“她幫夏然既是出于善良,也是對現有生存秩序的反抗。”觀眾看到的不是臉譜化的人物和簡單的“正邪對立”,而是一個被命運推入深淵的女性,在絕望中掙扎著保留最后一絲尊嚴。
從忙崖小鎮的封閉空間到角色的心理牢籠,《大風殺》在暴力的外表下包裹著對現代人精神困境的關懷。有人困于過去,有人困于欲望,有人困于身份……這是一次關于“困與破局”的影像思考,當銀幕上的槍聲漸歇,走出影院的觀眾或許會在某個瞬間,重新審視自己生命中的“忙崖小鎮”,以及那些“不得不做的選擇”。
“那些被風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緊我的心。”影片結尾,樸樹《且聽風吟》的旋律響起。這首誕生于2003年的民謠,以風為意象串聯起人的狂亂與釋然,就像影片中裹挾黃沙的狂風,既吹散了暴力與算計,也埋葬了那些“來不及遺忘”的悲傷與執迷。(見習記者 臧韻杰)
責任編輯:付琳
查看心情排行你看到此篇文章的感受是:
版權聲明:
1.凡本網注明“來源:駐馬店網”的所有作品,均為本網合法擁有版權或有權使用的作品,未經本網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摘編或利用其他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經本網授權使用作品的,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并注明“來源:駐馬店網”。任何組織、平臺和個人,不得侵犯本網應有權益,否則,一經發現,本網將授權常年法律顧問予以追究侵權者的法律責任。
駐馬店日報報業集團法律顧問單位:上海市匯業(武漢)律師事務所
首席法律顧問:馮程斌律師
2.凡本網注明“來源:XXX(非駐馬店網)”的作品,均轉載自其他媒體,轉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其他個人、媒體、網站、團體從本網下載使用,必須保留本網站注明的“稿件來源”,并自負相關法律責任,否則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3.如果您發現本網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識產權的作品,請與我們取得聯系,我們會及時修改或刪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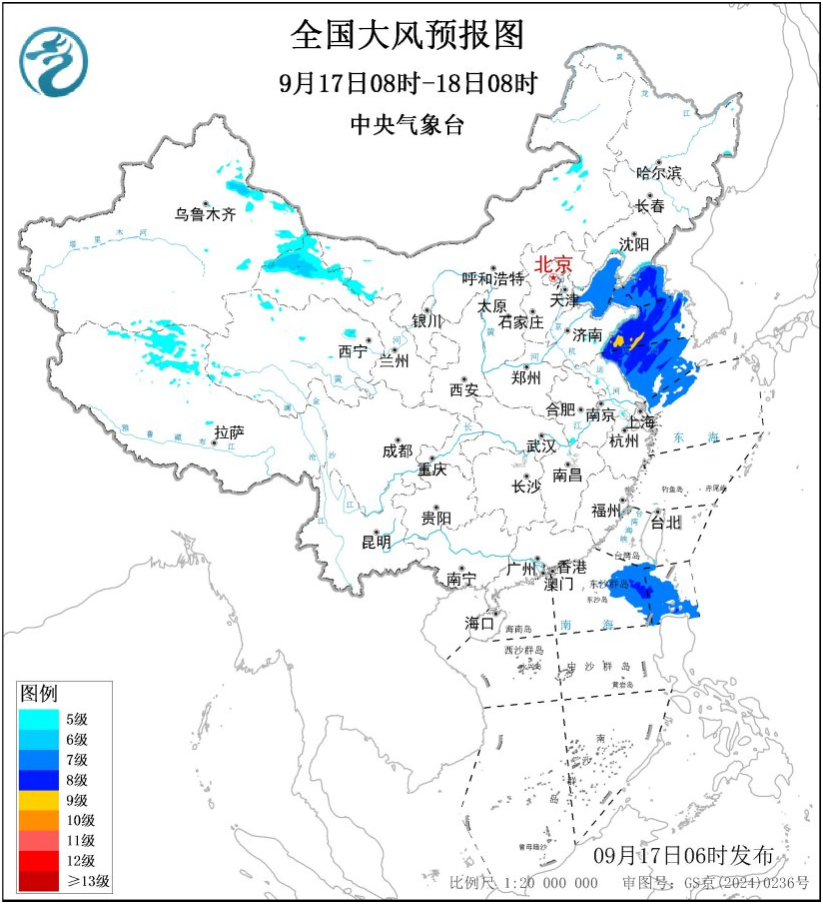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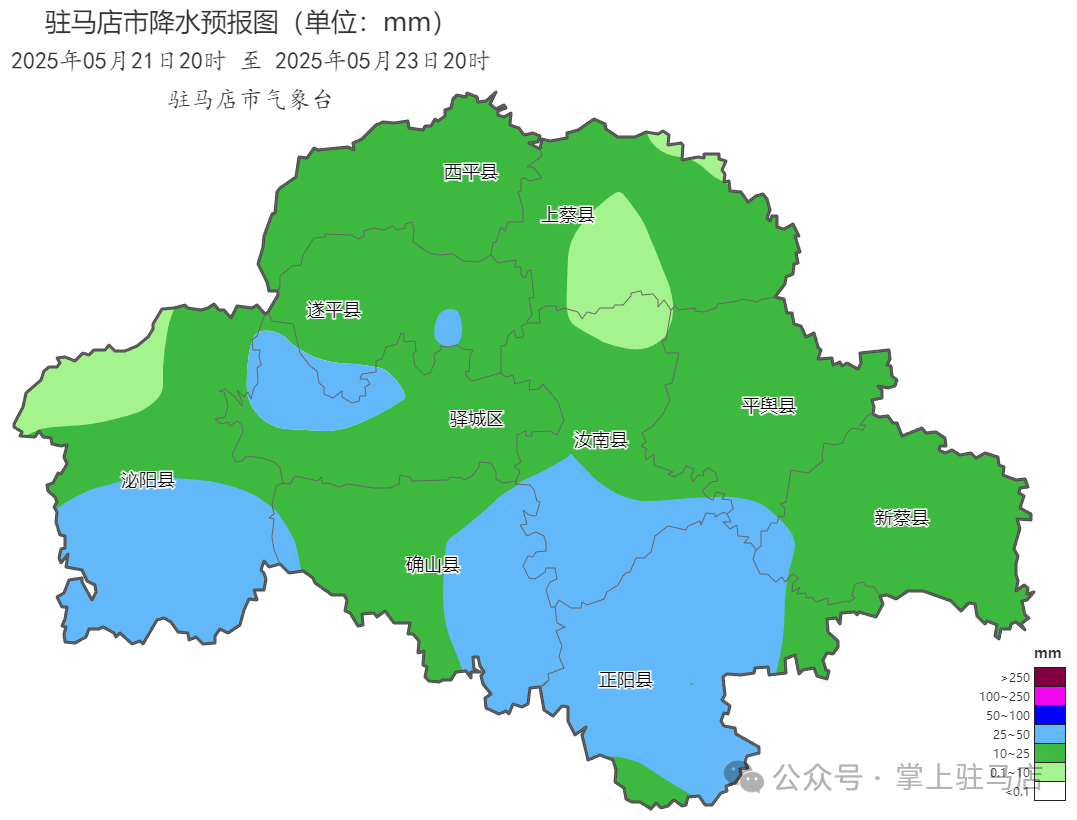
 豫公網安備 41170202000005號
豫公網安備 41170202000005號